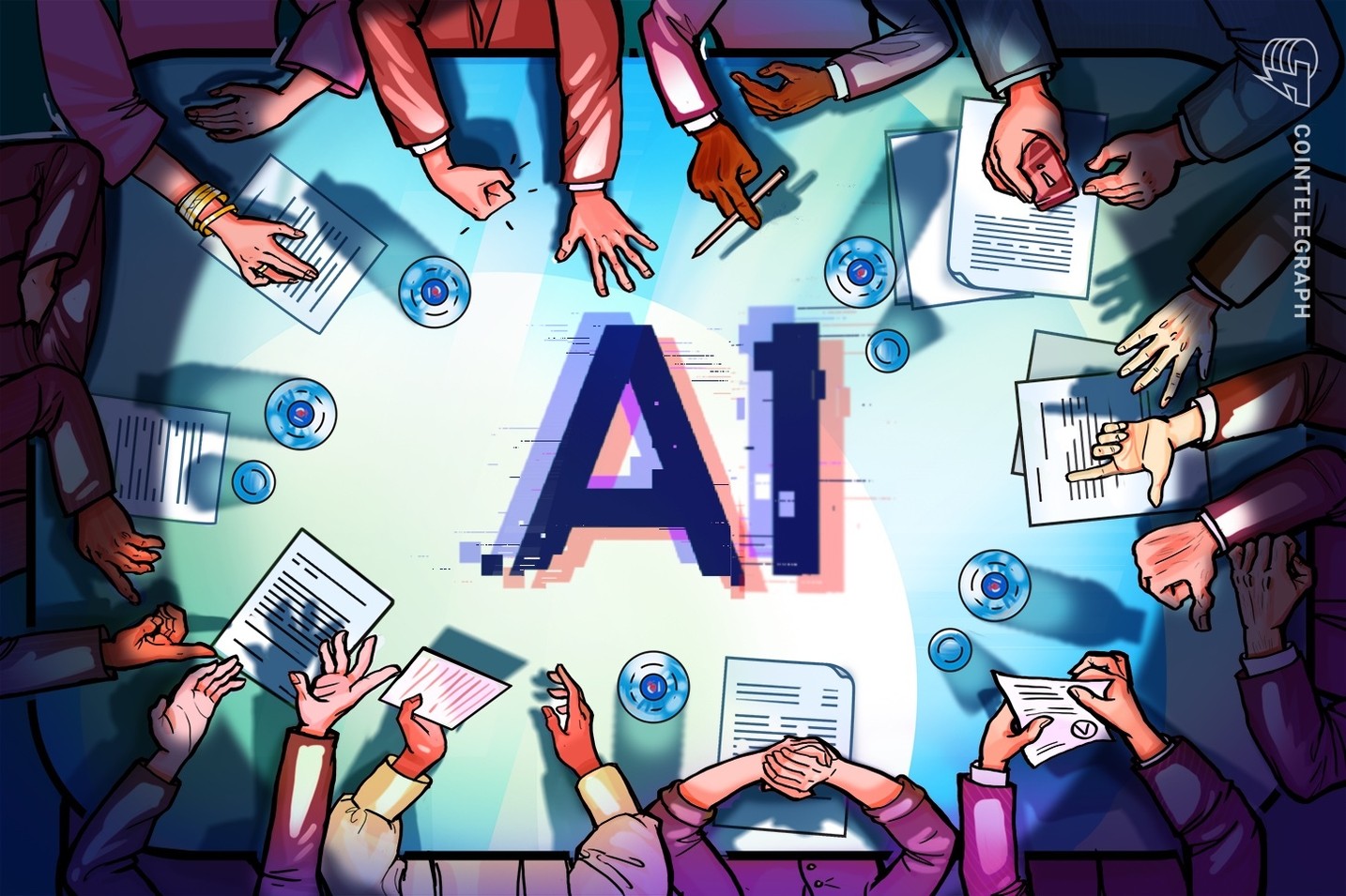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動察Beating,作者:律動編輯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2025 年 10 月 7 日,洲際交易所 (ICE) 宣布向 Polymarket 投資 200 億美元。
這家擁有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金融巨頭,成立於 1792 年,見證了美國金融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時刻。而 Polymarket,一家成立僅五年的公司,估值飆升至 900 億美元。
這筆交易的估值邏輯讓很多人困惑。
Polymarket 只有 30 萬月活躍用戶,平均每個用戶的估值達到 3 萬美元。作為對比,體育博彩巨頭 DraftKings 擁有 1000 萬用戶,市值 160 億美元,每個用戶估值僅 1600 美元,約為 Polymarket 的二十分之一。
更讓人不解的是 Polymarket 的業務本身。
打開這個網站,你會看到各種各樣的「賭局」:特朗普會不會在 2028 年再次參選?美聯儲下次會議會降息多少?某家科技公司的季度財報會超預期嗎?
人們在上面下注,贏了賺錢,輸了賠錢。這似乎和線上博彩網站看起來沒什麼兩樣。
但華爾街最保守的金融機構,為什麼要向一個看起來像賭博網站的平台投資 200 億美元?
答案藏在一個已經存在了近 40 年,但直到今天才真正爆發的概念裡,這個概念叫做預測市場。
它關於信息如何被生產、定價和使用,關於誰有權定義真相,也關於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如何做出更準確的決策,獲得更透明的真相。
這是一個從 1988 年開始的故事。
1988 年:192 個人如何打敗所有專家
1988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布希對陣杜卡基斯。
那一年,愛荷華大學的幾位教授做了一個實驗。他們邀請了 192 名師生,每人拿出不超過 500 美元下注布希和杜卡基斯最終誰會當選。
實驗的規則很簡單。你認為布希會贏,就押布希。隨著更多人參與,單注所需金額會上升;反之,當有人撤出時,單注金額也會相應下降。越早下注的人,可以在價格上漲後按當時的市場價退出,獲得收益。單注所需金額上限是 100 美元,這意味著,當押注布希的單注所需金額穩定在 65 美元時,市場的集體判斷是布希有 65% 的概率當選。
這個實驗被命名為「愛荷華大學政治股市」,後來改名為「愛荷華大學數字預測市場」。它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真實貨幣的預測市場。
結果讓所有人震驚。這 192 個普通人的集體判斷,比當時所有的民意調查都更準確,不僅準確預測了最終的贏家,連各州的得票率都非常接近實際結果。
更有意思的是,這種準確性並非偶然,它在此後的幾次選舉中多次得到驗證。
1992 年克林頓對老布希,1996 年克林頓對多爾,2000 年小布希對戈爾,愛荷華大學數字預測市場一次又一次地打敗了專業民調機構。
為什麼 192 個普通人能比專家更準?
傳統民調問的是「你會投給誰」。但人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可能出於社會壓力撒謊,可能臨時改變主意,可能根本不去投票。民調捕捉的是人們此刻的想法,而想法是飄忽不定的。
預測市場問的是另一個問題:你願意為這個判斷付出多少錢。當真金白銀擺在面前時,人們會更認真地思考,更誠實地表達。你可能嘴上說支持某個候選人,但如果讓你拿錢下注,你會重新審視自己的判斷。
更重要的是,市場會自動聚合所有人的信息。你可能了解你所在城市的情況,我可能知道年輕人的想法,他可能掌握某個行業的動向。當我們都用錢投票時,這些分散在無數個體頭腦中的信息,就被匯聚成一個數字。這個數字不是某個專家的判斷,而是所有參與者信息的加權平均。
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群體智慧」,當大量獨立個體基於各自的信息做出判斷時,其平均結果往往比任何單一專家更準確。
但這個實驗很快遇到了一個關鍵的合規問題:在法律上,這算不算賭博或非法證券交易。
美國法律對賭博和金融交易都有嚴格限制。愛荷華大學的教授們因此格外謹慎,將實驗規模控制在極小範圍:每人最多只能投入 500 美元,僅限學術研究使用,只開放政治選舉類市場。他們希望靠這樣的自我約束,避開法律的灰色地帶。
1992 年,他們終於拿到了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的一封「不採取行動函」。這封信的含義是:監管機構不會起訴你們,但這並不等於正式批准你們的行為。
也正因為這種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身份,預測市場在此後的十幾年裡始終被困在象牙塔中。
愛荷華大學數字預測市場一直維持著小規模運營,每次選舉只有幾千名參與者,總交易額不過幾十萬美元。它證明了預測市場的可行性和準確性,但也暴露了它的困境:如何在法律的夾縫中生存。
1999-2013:Intrade 的輝煌與崩潰
1999 年,兩位紐約期貨交易員 Ron Bernstein 和 Sean McNamara 看到了愛荷華實驗的商業潛力,創立了 Intrade,一個面向全球開放的預測市場。Intrade 不限制押注金額、主題和國籍,並將總部設在愛爾蘭以試圖繞開美國的監管。從 1999 年到 2012 年,Intrade 從一個小眾網站成長成為全球最大的預測市場,擁有來自 162 個國家的 8 萬多名會員。
2012 年美國總統大選,是 Intrade 最輝煌的時刻。
那一年,每個關注大選的記者、分析師、投資者,會盯著 Intrade 上「奧巴馬當選」的實時價格。這個數字比任何民調都更直觀,比任何專家預測都更快速地反映公眾情緒的變化。
10 月 3 日,奧巴馬和羅姆尼的第一場辯論。奧巴馬表現糟糕,全程被動挨打。辯論結束後的幾個小時內,Intrade 上「奧巴馬當選」的價格從 78 美元暴跌到 65 美元。這個跌幅遠超任何民調的變化,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有人認為是 Intrade 上的市場反應過度,也有人認為是民調機構太過遲鈍。
但最終,Intrade 正確預測了除佛羅里達和弗吉尼亞外的所有州選舉結果。
自那之後,《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都開始引用 Intrade 的數據,將它視為比民調更可靠的指標。那一年的 10 月和 11 月,Intrade 的月瀏覽量超過 5000 萬次,獲得了數百次媒體報導。人們開始相信,市場可能比專家更懂政治。
但輝煌的背後,Intrade 有三個致命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監管。
早在 2005 年,Intrade 就向 CFTC 申請在美國開設受監管的交易所,但 CFTC 的態度很曖昧,既不明確批准,也不明確禁止。於是 Intrade 就這樣在灰色地帶運營了十幾年。
直到 2012 年大選結束後,CFTC 終於起訴 Intrade,指控其向美國用戶非法提供包括黃金、石油在內的商品期貨合約,這違反了美國法律。Intrade 別無選擇,在一個月後關閉了所有美國用戶的賬戶,停止新用戶註冊,一夜之間失去了最大的市場。
第二個問題是流動性。
Intrade 的交易量其實並不大。2012 年大選前兩周,有人僅用 1.78 萬美元,就把羅姆尼的勝率從 40% 推到 49%。《華盛頓郵報》在那時曾發文質疑一個如此容易被操縱的市場價格是否有參考意義。
Intrade 回應稱,交易分散在 40 個賬戶之間,沒有任何單一個體購買超過 15% 的交易量,所以這不構成操縱,只是「市場訂單簿過於稀薄」。
但這並未打消人們的疑慮。更奇怪的是,Intrade 長期與其他博彩網站出現明顯價差,奧巴馬的勝率在 Intrade 上只有 60% 到 70%,而博彩公司的賠率早已超過 80%。
在正常的金融市場,這種差異會被套利者迅速抹平。理論上,如果 Intrade 上奧巴馬的勝率只有 65%,而其他博彩網站給出的賠率意味著 85% 的勝率,交易者可以在兩個平台上做相反的下注,即在 Intrade 買入「奧巴馬贏」,在博彩網站押「奧巴馬輸」。只要計算得當,無論結果如何,理論上都能鎖定收益。
但這個價差在 Intrade 上持續了數月。這並不是因為沒人發現,而是因為市場的流動性太差,根本沒有足夠的深度去修正價格。而這樣的市場,往往也最容易被操縱。
第三個問題是財務。
2013 年 3 月 10 日,Intrade 在官網發布公告,稱「因發現財務違規,暫停所有交易並關閉賬戶」。公告未說明細節,只援引愛爾蘭法律,表示被迫採取措施。
外界普遍認為,Intrade 在失去美國市場後陷入財務困境。交易量從 2012 年的一百萬筆驟降至次年的五萬筆,收入幾乎枯竭。公司曾計劃以「Intrade 2.0」重新上線,但最終沒能實現。2014 年 8 月,Intrade 宣布將永久關閉並退還所有用戶資金。
一個曾經輝煌的預測市場帝國,就此崩塌。
Intrade 的崩潰,暴露了中心化預測市場的三個致命弱點:監管可以一夜之間關閉你,流動性不足就容易被操縱,過度依賴單一市場會讓你非常脆弱。
但 Intrade 也證明了一件事:預測市場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在它最輝煌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每天都在使用它,媒體每天都在引用它的數據。問題不在於預測市場本身,而在於如何解決這三個致命弱點。
2020-2025:Polymarket 如何解決 Intrade 的三個問題
Polymarket 把整個平台搭建在區塊鏈上。與傳統公司不同,比如 Intrade 的交易記錄存在愛爾蘭的伺服器上,政府只要下令,就能讓伺服器關閉。而區塊鏈的賬本分佈在全球成千上萬台電腦上,沒有任何單一機構能讓它下線。所有交易記錄都公開透明,任何人都能查看、驗證,卻無法篡改。
這種架構帶來了三個關鍵優勢,恰好對應了 Intrade 當年暴露出的三個致命弱點。
第一個優勢是去中心化。
Polymarket 沒有中心化伺服器,所有交易都通過區塊鏈上的智能合約自動執行。即便公司本身被關閉,平台仍能運轉。合約代碼公開透明,任何人都可以調用,不需 Polymarket 的許可。
不過,「去中心化」很快在現實中受到了考驗。2022 年 1 月,CFTC 指控 Polymarket 未經註冊向美國人提供商品期貨交易,並處以 140 萬美元罰款。此後,平台開始通過 IP 識別等技術手段屏蔽美國用戶。
但與 Intrade 不同,去中心化讓 Polymarket 沒有被徹底摧毀。它繼續在全球範圍內運行,交易量不降反升。
2025 年 7 月,Polymarket 以 1.12 億美元收購獲得 CFTC 許可的交易所 QCEX;兩個月後,它獲准重返美國,結束了三多年的流亡。
Polymarket 的第二個優勢是流動性。
Intrade 依賴買賣雙方自行撮合,一旦市場冷清,單筆交易對價格漲跌的影響就會被放大,這也是為什麼當年只需 1.78 萬美元,就能把羅姆尼的勝率推高 9 個百分點。
Polymarket 用技術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它引入自動化做市機制,讓系統隨時提供流動性。無論何時買賣,都能立刻成交,即使是冷門市場也不例外。
這大幅提升了市場深度,也讓操縱變得更加困難。想撼動 Polymarket 上的熱門市場,所需資金可能是 Intrade 的十倍甚至百倍。2024 年美國大選期間,Polymarket 的日交易量一度超過 1 億美元,在這樣的規模下,價格幾乎不可能被單一巨鯨操縱。
第三個優勢則是透明度。
Intrade 的財務一直是個黑箱。直到平台崩潰前,用戶都不知道公司出了什麼問題,也不確定自己的資金是否安全。
而在 Polymarket,所有資金都在鏈上,任何人都能實時查看平台的資金規模、未平倉合約、交易量和流動性。這種透明度幾乎杜絕了財務違規的可能。如果平台挪用用戶資金,鏈上數據會立刻暴露,一切都無處遁形。
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Polymarket 迎來了它的高光時刻。
那一年,特朗普對陣哈里斯。整個選舉季,Polymarket 的數據被全球媒體廣泛引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彭博社》,幾乎每天都在報導 Polymarket 上的最新概率預測。在賓夕法尼亞、亞利桑那等幾個勝負難分的關鍵州,Polymarket 也幾乎完美地預言了最終的微弱差距。
11 月 5 日,選舉日當晚,當傳統媒體還在謹慎地報導著「選情膠著」時,Polymarket 上特朗普的勝率已經飆升到 90% 以上。
幾個小時後,特朗普宣布了勝利。
沒有任何一家傳統民調機構能夠媲美這種準確性和實時性。
那一年,Polymarket 的月活躍用戶達到 30 萬,月交易量達到 13 億美元,鏈上鎖倉價值達到 1.7 億美元。更重要的是,Polymarket 從一個加密貨幣圈的小眾產品,變成了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
但 Polymarket 也面臨新的挑戰。
2025 年 9 月,一個名叫 Kalshi 的競爭對手突然崛起。Kalshi 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徑:不走區塊鏈,而是走完全合規的路線。
它從 2018 年開始,經歷了六年的 CFTC 審批過程,最終成為首個獲得 CFTC 正式批准的預測市場交易所,打通了預測市場在美國的合規路徑。
Kalshi 主攻體育博彩市場。體育賽事頻繁,交易周轉快,很快就積累了大量用戶和交易量。2024 年 12 月,Polymarket 還佔據 95% 的市場份額,幾乎壟斷了整個預測市場行業。但到了 2025 年 9 月,Kalshi 的市場份額已經飆升到 65%,超越了 Polymarket。
Kalshi 的崛起,讓 Polymarket 意識到,技術優勢還不夠,監管認可和主流資本的支持同樣重要。
這就是 ICE 投資的背景。
ICE 的 200 億美元:華爾街看中了什麼
作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母公司,ICE 代表著華爾街最保守的一派。但就是這樣一家機構,卻選擇投資一個在外界看來近乎賭博的加密平台。
因為 ICE 從一開始看到的就不是賭博,而是信息本身的價值。
在 AI 和大數據時代,信息本身就是最值錢的資產。傳統的信息來源,民調、專家預測、智庫報告,都是「自上而下」的,由少數專家生產,普通人只能被動接受。
而預測市場提供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成千上萬人用真金白銀投票,市場價格就是他們的集體判斷。這個判斷往往比任何專家更準確,因為它聚合了所有人的信息、經驗和直覺。
ICE 要做的,就是把這些「群體智慧」包裝成金融產品,賣給機構投資者。
對沖基金需要知道下次美聯儲會不會降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會不會通過、某個地緣政治衝突會不會升級。跨國公司需要知道某個國家會不會發生政變、某個政策會不會出台。
這些問題,傳統的金融工具無法回答。股票價格反映的是公司價值,債券價格反映的是信用風險,期貨價格反映的是商品供需。但沒有一個金融工具,能直接告訴你「某個事件發生的概率」。
預測市場填補了這個空白。它給出的不是「是或否」,而是一個精確的概率。這個概率是實時更新的,隨著新信息的出現而變化,比任何專家報告都更快、更準。
根據 ICE 和 Polymarket 的協議,ICE 將成為 Polymarket 數據的全球分銷商,ICE 會向機構客戶提供實時的市場情緒指標、政治風險定價、經濟事件概率預測。這些數據可以被整合到投資決策模型中,幫助基金經理、風險管理者、企業戰略部門做出更好的判斷。
ICE 投資的另一個考量是數據的開放性。
Kalshi 雖然市場份額更大,但它是一個中心化的、受監管的平台。它的數據不是完全公開的,需要通過 API 獲取,而 API 的使用通常需要付費和授權。並且,它受美國監管約束,某些敏感市場可能無法開設。它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
而 Polymarket 是去中心化的。所有數據都在鏈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費獲取和使用,不需要 Polymarket 的許可。它可以開設任何市場,不受單一國家監管限制。比起 Kalshi,它是一個更開放的生態系統,全球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投注,任何人都可以基於它的數據開發新應用。
對 ICE 來說,Polymarket 不僅是一個交易平台,更是一個數據基礎設施。就像早期投資 Google 的人,看中的不是搜索引擎本身,而是它背後的數據和網絡效應。
900 億美元的估值,也反映了這個邏輯。
按常規估值邏輯,Polymarket 確實顯得過於昂貴。但 ICE 押注的,並不是它今天的業務規模,而是它在未來「信息金融化」時代的戰略位置。
Polymarket 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交易平台,而是一個新聞媒體、一個數據源、一個文化現象。它的估值,反映的更多是文化相關性和信息影響力。
那 30 萬交易用戶,只是消費 Polymarket 內容的數百萬人中的一小部分。每天有無數人打開 Polymarket,查看事件的最新賠率,卻並不交易。如今,高盛等金融機構也開始在研報中引用 Polymarket 的數據,且不再局限於美聯儲政策或政府停擺等宏觀事件
這就像早期的 Twitter 或 Facebook。它們的估值不是基於當時的廣告收入,而是基於它們可能成為的「社交基礎設施」。Polymarket 的估值,是基於它可能成為的「信息基礎設施」。
ICE 與 Polymarket 還計劃在「未來代幣化」項目上合作,探索預測市場在主流金融體系中的落地路徑。這意味著,預測市場合約有望被代幣化,在二級市場自由流通;其數據也可能被包裝成新的金融衍生品;更長遠的可能,是讓傳統金融資產與預測市場實現互通。
這些計劃的細節還沒有公佈,但方向已經很清楚,ICE 想做的,是把預測市場從小眾實驗,推向主流金融體系。
為什麼是現在?
預測市場的理念早在 1988 年就被證明可行,但真正的爆發,卻等到了 2025 年。
技術,終於追上了理念。
早期的區塊鏈技術又慢又貴,一筆交易要等待數分鐘,手續費可能高達幾十美元。普通用戶幾乎無法使用。那時也有人嘗試在鏈上搭建預測市場,但都因為體驗太差而失敗。
隨著技術的發展,交易確認只需幾秒,成本低至幾美分,操作體驗幾乎與普通網站無異。這些進步讓預測市場真正具備了可用性,交易更快、成本更低,用戶幾乎感覺不到區塊鏈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監管態度的轉變。
自 2012 年起,美國監管機構始終對預測市場持打壓立場。理由很簡單,因為預測市場看起來像賭博,而賭博在大多數州是非法的。
2022 年,Kalshi 嘗試上線「誰將控制國會」的預測合約,卻被 CFTC 以「類似賭博」為由否決。面對監管封殺,Kalshi 沒有退讓,而是選擇起訴監管者。這是預測市場歷史上第一次公司正面挑戰監管機構。
從那之後,風向開始轉變。2023 年,監管層開始討論預測市場的社會價值,一些學者和機構也呼籲重新評估其合法性。
2024 年,在 Kalshi 訴 CFTC 案中,聯邦法官裁定 Kalshi 勝訴,認為預測市場提供的是信息聚合服務,與賭博有本質區別。這個判決為整個行業打開了新的空間。
2025 年,CFTC 批准 Kalshi 全面運營,並結束對 Polymarket 的調查。Polymarket 也因此獲准重返美國市場。
監管態度的轉變是多種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
一個原因是,監管機構逐漸認識到預測市場的信息價值。2024 年大選,Polymarket 和 Kalshi 的預測都比傳統民調準確,這讓監管者意識到,預測市場不是單純的賭博,它確實在生產有價值的信息。
另一個原因是國際競爭。如果美國過度限制預測市場,這個行業勢必外流。新加坡、英國、瑞士等國正積極吸引金融科技企業,美國不願輕易喪失在這一新興領域的主導權。
ICE 的投資進一步印證了這種態度的變化。當華爾街最保守的力量開始擁抱預測市場時,監管機構也很難再把它視為「非法賭博」。ICE 的背書,為預測市場帶來了新的合法性與主流認可。
從「專家說了算」到「市場說了算」
從 1988 年愛荷華大學的 192 個人,到 2025 年 Polymarket 的 30 萬用戶,預測市場走過了 37 年。
這 37 年,見證的是一場信息權力的轉移。
現代社會的問題從來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而且真假難辨。
傳統民調頻繁失準。2016 年美國大選,幾乎所有民調都預測希拉里會贏,結果特朗普當選。2020 年,民調預測拜登會大勝,結果選情非常膠著。專家的預測同樣如此,疫情、經濟、地緣政治,最終的走向往往與他們的判斷背道而馳。
他們的預測被媒體廣泛報導,被決策者採納,被公眾相信。但他們經常錯,而且錯了也不用付出代價。
預測市場給出了一個新的答案,你不必相信任何個人或機構,因為你可以相信市場。
在這裡,任何人都可以參與預測,但你必須為你的判斷付出真金白銀。對了,就賺錢;錯了,就虧錢。這種機制,讓「預測」從一種權力,變成了一種責任。
你不需要是經濟學家,也可以判斷美聯儲是否會降息;你不需要是政治學者,也可以判斷特朗普會不會贏。每個人的判斷,會匯入市場價格,匯聚成一種群體智慧。而這種智慧,往往比任何單一專家都更準確。
擁有內幕信息和判斷優勢的人,會重金押注他們提前知道的結果,而這反過來又提高了市場預測的準確性。
一個經濟學家也許通曉宏觀理論,卻未必了解某個小鎮的失業狀況;一個政治學者也許熟悉選舉制度,卻不一定知道年輕人在想什麼。而預測市場,把這些分散的知識和經驗匯聚在一起,形成一個更全面的判斷。
這種機制,讓預測市場成為一個自我進化的系統。它不依賴中心化的權威去判定誰對誰錯,市場本身會獎勵正確的判斷,懲罰錯誤的判斷。
對普通人來說,預測市場還意味著一個更透明的世界。
你可以實時看到「市場認為某件事發生的概率」,而不是被動接受專家的說法。你能看到這個概率如何隨著新信息的出現而變化,從而理解市場是如何消化信息的。這些數據為個人決策提供了新的參考,無論是投資、創業,還是日常的人生選擇。
預測市場還意味著更公平的遊戲規則。
在這裡,你的判斷和華爾街分析師的判斷擁有同樣的權重。只要願意為它付出真金白銀,你的看法就能影響市場價格。這與傳統的信息生產模式截然不同,在傳統體系中,只有少數人的聲音能被聽見,只有少數人的判斷能影響公眾認知。而在預測市場,每個人都能發聲,每個人都可以用資金表達自己的判斷。
ICE 的 200 億美元投資,標誌著預測市場從「邊緣創新」走向「主流基礎設施」,從「灰色地帶」走向「合法產業」,從「加密貨幣圈的玩具」走向「華爾街的工具」。
但更重要的是,它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代,信息不再由少數專家壟斷,而是由市場生產;真相不再由權威定義,而是由群體智慧決定。
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